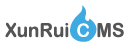全世界艰难系数最高的医生,在战场上和死神抢人_ZAKER新闻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加沙。
据报道

采访、撰文 | 三金
最近,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加沙。
据报道,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爆发前,加沙有超过70%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为农业无法满足粮食的基本需求,常年依靠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维持生活,平均每日有500辆货车进入当地。但今年3月2日至今,进入加沙的物资总数加起来也没达到这个数量。
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席卷了加沙。医生报告急性营养不良比率高到前所未有,甚至医生也在挨饿。与此同时,粮食分发点成为特意设置的"死亡陷阱",以色列军队对前来领取食物的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施加无差别的暴力。

在加沙人道基金会运营的粮食分发点,人们要获得食物往往要冒着生命风险。照片拍摄于2025年7月25日 ©MSF
近年来,持续的战争和气候变化影响着许多国家,使动荡成为一种常态。
不只是加沙,苏丹的武装冲突也已经持续两年,战火波及全境18个州中的15个,安全状况持续恶化。
缅甸在今年3月发生7.9级地震,目前还在复原和重建过程中。央视新闻报道,这是全球近十年来大陆最强地震,也是今年全球发生的第17次六级及以上地震。

无国界医生在苏丹喀土穆州的住院营养治疗中心里,三岁的小患者在妈妈的陪伴下住院治疗。© Tom Casey/MSF
生活在和平国度的人们很难想象:或许此刻有人正在饿死,有人生病受伤得不到救助。
废墟之中,一群人正在为救援而奔波。"无国界医生"组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每年会派出3000名救援人员,和4万多名当地员工并肩在全球约70个国家服务,至今已经有30多名中国内地的"无国界医生"成员在前线救助。除了医护人员,参与者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在加沙,他们看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严重爆满,四、五名婴儿需要共用一个保温箱";在缅甸,他们设法给当地居民提供干净饮用水供应、适合的避难场所和心理健康支持;在苏丹,因为一名员工被绑架,他们被迫暂停在当地的所有工作至少六周……

在加沙南部的纳赛尔医院里,病人人满为患。床位短缺,很多伤者只能栖身在走廊和病房外。图片拍摄于2025年8月12日 © MSF
每年的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而即便对于大部分医生而言,"无国界医生"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们好奇,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会有哪些奇特的经历?面对难以撼动的政治局势,个人的力量还可以做什么?他们是否也感受过工作带来的迷茫无助、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借由《无国界医生手记》出版的机会,我们采访到曾经参与过伊拉克项目的重症医学科医生刘一云和无国界医生驻北京办公室的魏保珠,听她们讲述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在故事背后,作为人道救援者的选择、怀疑与挣扎。

《无国界医生手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出版。
哪怕做着一份大众看来十分伟大的工作,他们也经历过意义感的丧失与重建,感受到人的韧性逐渐被削弱,却依旧无法转身离开,"他们不是上帝,虽然他们希望自己是;他们只是凡人,试图疗愈凡人。"

一家中国顶级三甲医院,
一间死亡率100%的病房
刘一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本硕连读7年,然后考博,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顺利进入上海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一待就是9年。
读书和工作的这些年里,医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重症医学科使用着高精尖的仪器和设备,大家抱着"不能输给疾病"的决心在ICU里挽救患者生命。但刘一云常常想,如果离开这么好的条件支持,在资源缺乏的地方,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2020年,她从瑞金医院辞职,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生。"世界上有很多得不到医疗救助的人生活在绝望中,也许只要一个医生过去,就可以给他们带去希望。对当时的我来说,成为这样的医生,能比我在中国最好的三甲医院里发挥出更大价值"。
很多同事和朋友不理解,哪怕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怎么会有人放弃稳定的工作去做一件没有保障的事情?而当她亲身前往伊拉克参加第一次项目,发现当地情况远比她想象的更加复杂,这次选择也深深改变了她的生活。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和书籍内容整理:
2020年10月,我从上海飞到香港,再飞到多哈,花了21个小时才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这是一项紧急任务,我到的时候,当地物资、人手都紧张,而有的同事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我们需要帮助当地控制传染病流行,队伍里像我这样的国际员工大概十来人。
走出巴格达的机场,大概是凌晨五六点钟,天还是黑的,我坐上无国界医生的车辆去隔离酒店。路上车不多,两旁街景看起来像是中国一个普通的三线城市,空气里是一片祥和的味道,跟我想象中的伊拉克很不一样。
但很快我发现,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座城市。我们酒店楼下就停放着一辆坦克,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一旁。从酒店去工作的医院,路上有很多岗哨、坦克和士兵,我们的大巴车还被拦下来过,要求查看证件。

工作的金迪医院。©刘一云MSF
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地在巴格达,其间也去过摩苏尔。3000多年前,这里是古亚述王朝的中心,有很多历史遗迹,因为春秋两季温度相近,又被称为"双春城"。现在那里战争的痕迹更加明显,左边是枪炮下建筑物的断壁残垣,右边就是当地居民在工作的小店。
当时伊拉克每天有接近4000例传染病新发病例,每周约500人死亡,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和当地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医院里开设传染病感染治疗病房,接收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
在此之前,伊拉克的医疗教学系统里是没有重症监护专业的,和我并肩工作的当地同事都不是ICU医生。所以我在诊治患者之余,还要给他们组织课堂培训和床边培训。
虽然一开始就接受了很多关于当地情况的简报,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第一天走进医院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宿舍换好ICU内穿衣去医院,在队友面前戴帽子口罩,穿一次性隔离衣,然后戴面屏。在国内,起码还要穿一件防护服。我本以为会到下一个地方进行新一轮穿戴,没想到队友直接走进了病房。
那一刻,我心里十分恐慌:完了,我一定会被传染!已经在当地工作一个月的队友们表情却都十分淡定,我只能告诉自己:他们能做到的,我也可以。

刘一云医生和当地同事。图片来源:刘一云/MSF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ICU病房,病人和病人之间用帘子隔开,一开始医院有24张床位,总是满员,在我们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的时候,后勤部门的同事正在抢时间将附近新的大楼改造成有36张床位的治疗点。
在我们搬去新大楼之前,大部分病人都会死亡,只要一个病床空了,马上会有新的病人进来。由于医护人员短缺,这里的护士只做治疗的工作,由病人家属24小时陪伴患者,这很容易造成感染,我们只能提醒家属做好防护。
最难的时候,一个口罩要戴一天,我尽量不让口罩沾湿,就算因为病人去世而崩溃哭泣,也只能默默等眼泪流干;面屏也只能反复消毒,最后挡板都变得模糊。
任务刚开始第一个月,因为没有无菌手套供应,我们直接把消毒液往手套上撒;医院里药品不全,一些救命药也需要家属到外面的药房里去买。
更残酷的是,整个病房只有一台心电监护仪,医生们需要一起评估,按目前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的挽回机会极小,就得把他的监护仪拆下来给另外一个挽回率更高的病人用。
这时候有家属会问:为什么要把这个拆下来?为什么不给他用了?
这对病人、家属、所有医务人员而言都十分痛苦。我很清楚,这个患者如果在上海的ICU是可以挽回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无法得救。

刘一云(左)在医院病房内查看病人状况。©Ghada Safaan/MSF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接手的危重症病人几乎是人人死亡。每天清晨踏入医院,我总会听到病人死亡的消息,只不过数量是几个而已。虽然在ICU工作多年,我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见证这么多生离死别。
家属们会围着我,他们想要听到患者的好消息;当地医生也格外关注我的一举一动,迫切希望从我这里学习如何把同胞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而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责与自我怀疑:
我是来帮忙的,为什么什么也做不了?是不是如果换了别的医生可以更多帮助到他们?我来这里真的有意义吗?
有一次,我和当地医生聊起这些消极的想法,他告诉我,在没有这个项目之前,大量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被送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处理,每个患者都在死亡。现在真的有患者能被救回来了,其实他们很感激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当地医生在精神上显得格外强大。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看到过真正的悲惨与绝望。
我在摩苏尔进行救助慢性创伤患者项目时,很多患者都是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四肢创伤,一位当地医生告诉我,在战争期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治疗被各种炮弹伤害的病人,接触多了,他一闻味道,就知道病人是被哪一种武器击伤的。
队伍里有一位德国护士也关注到我的情绪,作为一位项目经验丰富的无国界医生,她有一次在聊天时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不要认为自己很伟大,不远万里来这里拯救生命,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做到最好,也只是提供了一点帮助。"

晨会上,医护人员交换患者情况更新。 ©Hassan Kamal Al-Deen/MSF
我曾经认为,医生放弃的时候才是患者真正失去救治希望的时候。但后来我开始接受,其实所有人都在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下做到了最好,我必须放下这些心理负担,打起全部精神救治眼前尚有一丝希望的病人。
而当我和当地医生解释采取姑息治疗的理由,和家属详谈为什么要将患者的治疗目标从挽救生命转为减轻痛苦时,我看到他们不仅接受,还恳切地感激医生们做的一切努力。
在所有人的坚持下,我们接收的患者的死亡率终于从近乎100%降到60%。
我学医和工作多年,在伊拉克的工作,却让我重新回想起自己学医的初心。我崇拜的一位欧洲的重症医学科的教授在讲课中说过,在给病人镇静镇痛之前,要先拉着他的手,告诉他,你现在是安全的,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医生总是会对救回来的患者觉得理所应当,对救不回来的患者耿耿于怀。但是在做了一切努力却依旧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给与安慰和帮助。

刘一云日常旅游时的生活照。 图片来源:刘一云

恶劣的情况是前所未见的
1971年,一群法国医生在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灾难后,与几名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7年,无国界医生在广州招募工作人员,已经工作两年的魏保珠加入其中,负责传播。大部分时间,她在办公室内,接收前线同事们发来的消息;有时也会前往前线项目,去尼日利亚、阿富汗、黎巴嫩、约旦等地探访和支持项目工作。
在她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最理想的状态,无国界医生会在一个地方进行紧急救援,与当地医护人员一起工作,情况稳定后,将工作交接给当地组织,再去往其他项目。但随着冲突、疫病、天灾等危机卷土重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无国界医生已经工作了几十年。
刚开始工作时,她和刘一云有过同样的困扰,她问同事:"这里冲突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几年,你刚刚救助的病人,可能转头死在战争中,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人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曾经有一位瑞典的无国界医生见证了塞拉利昂的11岁童军无情杀死孕妇,回到祖国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在《无国界医生手记》一书中写下:
历史告诉我们,高度的文明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保障,情势是会突然改变的。原本是人人都遵从的绝对道德规范,一下子就可以失去制约能力……对在落后地区无辜受害者的承担,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承担。
以下是魏保珠的讲述: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致力为受武装冲突、流行病、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被排拒在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工作的地方大多医疗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力求达到当地卫生部门推荐达到医疗水平。
比如刘医生去到的伊拉克,当地没有重症监护ICU,我们不能把发达地区的系统空降到这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根据当地现有的医疗设施开展服务,和当地人一起工作,为他们提供培训,等情况稳定后,再交接给当地人,让他们可以继续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
作为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伊拉克医疗系统的重建还需要很长时间,有同事还在当地提供医疗护理,但整体来说,相比刘医生去的时候,我们目前在伊拉克的行动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加沙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
从2023年开始,以色列对加沙开展了长达22个月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快两年了。我们同事每天都在当地救治伤者,有的是武器带来的伤口,还有因为生活条件恶劣带来的疾病,比如说腹泻和皮肤病。但在巨大需求面前,我们的工作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今年3月,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的围困。按照《国际人道法》,冲突双方需要尊重医疗设施、医疗人员和救护车辆。但我们看到加沙当地的医疗设施不断遭到袭击,一半以上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也有工作人员遇难的消息传来。
现在,当地食物、燃料、医疗物资都被封锁很难运进去,关于生活的必要设施都被剥夺,所谓的加沙人道基金会运营的粮食分发点不断有平民被枪击,然后送来医院,医生人手严重不足,但还需要为患者提供救助。
我们的报告显示,无国界医生设施中接受营养筛查的六个月至五岁儿童,以及孕妇和哺乳妇女中,有多达四分之一被诊断为营养不良。

Fadi是无国界医生在Deir Al Balah的临时医院的一名患者,他描述了自己前往所谓的加沙人道基金会援助分发点,试图领取食物却受伤的经历,"我去拿些吃的,他们却朝我的眼睛喷辣椒喷雾。现在医院里都是受伤的人,只有我成功地拿到点食物,我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就是这些——一些米,一包意面,一瓶水。拍摄于2025年6月6日 © Nour Alsaqqa/MSF
早从1989年开始,"无国界医生"便在巴勒斯坦开展人道救援行动,为当地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医疗和心理健康支持。
2013年,我在黎巴嫩的救援项目遇到过一位在加沙工作过的英国心理医生,据他所说,他在加沙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因为炸弹落在自己家旁边而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一般而言,接受四个月的心理治疗后,情况会有改善。但那是局势相对稳定时的加沙,现在已经大不相同。
每一个前线同事们都说,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

2025年7月25日的加沙。©MSF
2024年,香港的助产士苏衍霈两次前往加沙,参与当地纳赛尔医院的妇产科、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和性暴力门诊等部门的重建,一次项目为期六周,这已经是一个人濒临疲惫的极限。她必须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生活和工作,在外停留和行走都十分危险。
5月,她第一次去到纳赛尔医院。这所医院2月份被军队轰炸,每个门窗都是破烂的,还有一些白布包裹的遗体发出臭味,没来得及处理。
在她抵达医院之前,我们的工程人员已经去过该医院,确认建筑本体完好,可以从废墟变成一个医疗点。但看着破烂的大楼,苏衍霈原本想着可能等她离开,这里都没有办法重建,但仅仅一个星期,医院就开始接收病人了。
有孩子在医院呱呱坠地,当时团队的所有人都哭了。当时人们都希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有人都满怀希望。
9月,苏衍霈第二次去加沙,待到10月底,当时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她看到当地人眼里已经没有光了。时间过去一年,没有任何的希望,人们都开始变得麻木。时间太长了,很多原本关注巴以冲突的人们也偏过头去,不愿再看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
今年1月,加沙终于实现停火。很多同事分享他们看到的景象:大街上的孩子在跑在跳,唱着"回到家乡"的歌,每个人都很高兴。在此之前,这里已经400多天没有任何庆祝的声音。很多人在这样的欢声笑语里泣不成声、百感交集,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失去,所有的悲伤都开始浮现。
但这次停火太短暂了,现在的情况只会比之前更恶劣。

以色列军队向前往加沙人道基金会分发点的人们开枪后,无国界医生在马瓦西的卫生中心里接收到了大量伤者,有的抵达医院时已死亡。他们都是为了给家人获取食物前往分发点。照片拍摄于2025年8月3日 ©MSF
从2023年10月到现在,我每周都会收到来自加沙的消息。一开始简报里提到,医院里有很多年纪特别小的患者,他们是整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独自来到医院,医生们用 WCNSF(wounded child, no surviving family) 这个缩写给他们标记,意思是 "没有家人幸存的受伤儿童"。
那代表着他已经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我会很悲伤,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孩是很难活下去的。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太难受了,就写了一首很幼稚的小诗,用表达帮助自己缓解痛苦。
《世界的小花园》
我希望地球上的人们吵架的时候
会一起种下凤仙花
浇水、施肥
开出无数个粉色蓝色白色嘟着嘴的小喇叭
说出所有的难为情和对不起
我希望地球上的人们悲伤的时候
会种下蓝雪花
那喷涌的花儿会像辽阔的海洋舒展
带来清风和小鸟的呼吸
我希望人们在绝望的时候
就随便种点什么吧
就算是一棵无名小草的叶尖
也有担起一颗清澈露珠的力气
工作多年,除了那些悲伤痛苦的故事,项目中也有些文化差异带来的趣事。比如有些地方医疗设施简陋,我们在当地医院提供B超服务,很多人没有见过,传来传去变成了"无国界医生那有一个很神奇的机器,你照一照就可以怀孕啦"。
还有一些事,会让你感受到世界的参差。例如在利比里亚,曾经有同事工作的地方小孩的夭折率很高,所以孩子刚出生时,家人会按照星期几给孩子取名,比如星期一出生的孩子就叫"星期一",正式的名字要等孩子活过一岁后才有。
随着中国医生越来越多,每个人展示出来不同的性格,我去项目上时也会听人聊起他们。比如在阿富汗,时不时还有人说起"要是那个中国来的女医生在的话,这个病人她一定不会轻易放弃";
我去埃塞俄比亚,还有人聊起某某医生很酷,穿着人字拖爬山,比装备齐全的队友们还快,是个风一样的女生;
在南苏丹,当地人跟我说,有个中国医生很幽默,他在的时候,每天都把大家逗得很开心,他走了后大家都很想他。

两年前,快速支持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和针对平民的袭击、流离失所、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暴发和气候冲击使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迫切需要人道援助和保护服务。© MSF

苏丹的战事和极端天气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国界医生提供针对营养不良、腹泻和疟疾的医疗护理作应对。图为无国界医生在流离失所的人们聚集的地方提供如何避免霍乱的健康资讯。© Faiz Abubakr
我在阿富汗还看到一些六七十岁的同事,他们选择在退休之后加入无国界医生,这份事业并没有年龄限制,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真的不用着急。"条条大路通罗马",你需要问自己想不想要去罗马。
我从大学时就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对志愿工作很感兴趣,加入无国界医生办公室的工作让我看到了危机之地人们的坚韧和团结,也看到了许多救援人员们讲述的悲欣交集的故事。
成为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并不是轻松的旅程,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正在被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摧毁,且无从修复。但还是有人不想转身离去,尽其所能,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感谢"无国界医生"组织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