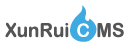【光明时评】数字化让文化遗产焕发更多活力_ZAKER新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日
【光明时评】
作者:王思渝、张剑葳(分别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日,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近百个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进行了展示。让文化遗产获得 " 数字生命 ",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乃至社会价值,且脆弱又无法再生。如何判定并且彰显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以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保护和延续文化遗产是重要议题。如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测量、记录、规划、日常管理、监测、展示利用等开辟了新的路径,成为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极大推动了文化遗产测量和记录技术的革新,这种革新有可能推动学术界关注过去未曾关注的信息,从而带来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深化和补全。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存有大量隋代至辽金时期的珍贵石经,历经千年,许多石刻经文已难以辨识,而 " 微米级 " 微痕增强成像数字技术的应用,让原本已经漫漶不清的文字有了识别的可能。位于石经山顶五台之一的曝经台,是辽代碑刻记载的 " 曝经祈福 " 之地,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 " 无字石台 ",经多角度光源矩阵扫描与算法增强,首次揭示其表面存在大量雕刻文字,颠覆了此前的认知。
数字化还能拓宽文化遗产展示层面的可能性。传统的文化遗产展示,通常需要在本体上施加建设性工程。为避免破坏遗产本体,或避免展示工程的干预手段在视觉上对遗产的历史感、氛围感产生打扰,人们有时会选择放弃对文化遗产进行阐释。这种情况在考古遗址的展示中尤为常见,观众也常因此抱怨 " 只看到一些土堆,什么也没有 "。在学术界,对于已经失去形象的文化遗产是否应在实体层面进行原址、原样的 " 重建 ",一直是争论的一大议题。在此背景下,以数字化为支撑的虚拟重建和沉浸式漫游,意义更加凸显。其既能帮助当代观众直观地理解遗产对象,又不会对遗产本体产生过多的干预,避免让观众对遗产本体产生 " 真假不分 " 的错觉。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交互性数据库等技术的运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走向 " 智慧 " 或者 " 交互 ",使得当代观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一向度的 " 观看 "" 欣赏 " 或者 " 学习 "。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在这方面提供了示范。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等机构发起的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监测公众参与活动,鼓励公众志愿者将日常拍摄的大运河照片通过小程序上传,如此做法既能弥合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在日常监测上面临的困境,对于提升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也大有裨益。
相较而言,博物馆展览环境更加可控,在对文化遗产相关信息进行数字化方面也涌现出更丰富的成功案例。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 运河上的舟楫 " 展在搭建数字沉浸展厅的同时,在线上融入对实物模型的展示,力求虚拟体验和对实体之 " 物 " 的观看相互补充,如此既能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有更为全面的阐释,又能让观众借此形成更丰富的体验。对于许多位于文化遗产地现场的博物馆而言,其在展品资源上并不一定丰富,有时或陷入无 " 物 " 可展的尴尬,如 " 运河上的舟楫 " 一般的模式便为平衡此类尴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此外,湖南博物院举办的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展,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山西永乐宫文物精粹暨数字艺术大展等,也是数字化展示方面备受关注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越是发展,对技术应用的审视越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化应用,也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数字化监测形成了大量的日常数据,如何将这些数据应用到遗产地的风险评估或应急预案制定中,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机制。数字化展示能够为观众带来更为沉浸、具身的体验,在市场化环境中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是,观众数量层面的 " 火热 " 并不一定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或者教育正向相关。当一处遗产地的数字化展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展示的重点是否还围绕着遗产价值最为核心的部分展开,还是转移到市场营销逻辑层面的 " 卖点 " 上?被市场快速接受的数字化产品,是否能反哺遗产本体,还是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流通?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今天,其便捷与酷炫,是否会助长关于遗产不同信息的杂糅与拼贴,从而创造出一个从未真正出现过的 " 历史 "?这些追问值得我们不断思考。
当前,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全流程中的意义已经被更多 " 看见 "。未来,我们应坚持以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与传承为核心,数字化技术作为手段,让文化遗产焕发更多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与期盼。
《光明日报》(2025 年 10 月 20 日 02 版)
[ 责编:孙宗鹤 ]